重庆城市精神丨蒋萍:柳暗花明又一村
2025-03-17 06:32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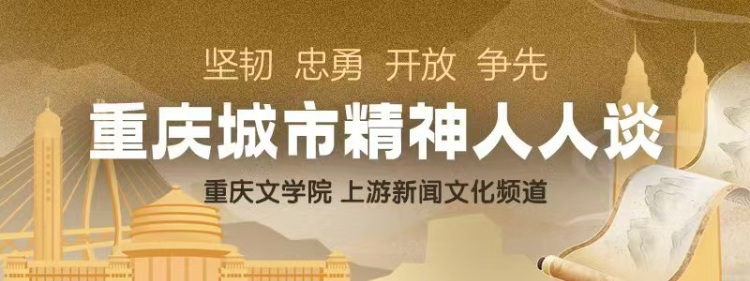
柳暗花明又一村
文/蒋萍
人生的旅途,从来不是一帆风顺,影响一个人能走多远的,是韧性。
——题记
一直以来认为自己总能受到幸运之神眷顾般做什么都比较顺利,然而在考教师资格证时却令我失落颇久。没有通过面试的我,在家里一度萎靡不振。母亲见我心情不好,劝我一起回老家走走。
木洞古镇,始于唐宋,兴于明清,因水而兴的木洞镇是连接川渝的重要水码头,是长江水运中转站和商贸集散地。我和母亲走在曾经居住的穿斗房下,沿着石板路来到河街,宽阔的大道,独具风格的民宿,还有整齐的河滩,丝毫看不出这里以前长满了花草,曾经上船下船的小坡上总是搭着两排雨棚,里面冒着豆花的热气,木洞豆花饭是人们舟车劳顿后的裹腹美食。如今的这里,已变成了旅游景点。
木洞古镇的风貌,正是重庆这座城市的一个缩影。重庆,在中国西南部独具一格地发展着,既不像北方那般雄浑大气,也不似寻常的南方一般细腻温柔,在山水环绕中,豪爽与温婉并存。而这里的人,似乎也在一条条街道,一座座桥梁,一道道江海,一层层山峦中孕育出自己的性格。
一句“木洞豆花饭,胀得精叫唤”的方言,恰到好处地展现出重庆人的热情与豪爽,说的是吃木洞豆花可以把人吃得肚子胀鼓鼓的,因为实在是太好吃了。只要听到吆喝声,我便挪不动步子,脚就跟着香味飘去。老板总是眉眼舒展地端过碗碟,麻溜儿地舀起嫩滑的豆花,调和着蘸料。
“来啰——”山城的语调和发音,并不是粗鲁粗壮的,而是一种自由奔放的敞亮。湿热的空气,令人们更追求辣、鲜、香的羁绊,激发着大家的热情。
“赶”豆花是我认为吃豆花饭最有趣的地方,何为“赶”?“赶”则是一个动作,因豆花内含大量水分,故而滑嫩无比,若直接用筷子夹,豆花会瞬间分崩离析,我也是学了许久,才能将其“赶”入蘸碟。用筷子将一指头大小的豆花轻轻地朝碗沿反复挤压,待豆花内水分慢慢变少,豆花变小些时,再夹至早已准备好的蘸碟中。此刻,豆花仿佛沉睡已久,肆意妄为地在辣椒和香料的气息中伸着懒腰,热乎乎的豆花和着油亮亮的辣椒,将跋山涉水的疲惫一口勾销,再来一口“窖水”,一切酸甜苦辣似乎回归质朴。
生活总有起起落落,就像豆花一样,以前人们用石磨推拉豆子,如今有了科技的加持做豆花更容易。但是简简单单的一粒豆子,想要蜕变成豆花,却要经历七八小时的浸泡,耐心地研磨。
小时候,外婆和妈妈常常一起用摇架一点儿一点儿将烧开的豆浆过滤出豆渣,此时的我,最爱用一个碗接住豆浆,加点儿白糖,满足地享受豆浆的暖与香。豆渣过了二道浆水后,拧干,加热,加卤水,便可以开始少量多次地点豆花。这是一个漫长的等待,却是豆花成型的关键。最后,用簸箕压实成型的豆花,把“窖水”舀一些出来,豆花算历劫完毕。接下来准备压豆腐,将豆花舀到蓖子里,过滤出水,上面压一块放着一碗水的菜板,静待着,豆腐在压力的渐渐增加下有了形状。
豆子的旅程告一段落。剩下的豆渣也不能放过,可以用来炸丸子,锅上的豆浆锅巴还可以煎来吃。可以说,豆子一身都是宝。
豆花较绵软,不松散,有豆子本身的回甜味。正是因为豆花的形成如此考验耐性,人们才会更珍惜那一口生活的酸甜苦辣。
母亲依依不舍地放下筷子,哈着气:“老板,这个味道好巴适!”一碗豆花饭,将回忆变得清晰,也将未来徐徐勾勒。
回来后,我重新回顾了这次失败的原因,是自己的骄傲忽略了课后的积累,于是我将所有的语文书都拿出来,每一篇课文都写了一次简案,甚至书本后的附录也钻研了一次。当我胸有成竹地再次站在评委们面前,无生试讲了鲁迅的《社戏》一文。在答辩时,考官提问我对“意境”和“意象”两个词语的理解,我想到自己曾在写简案时查阅过,便将各自的含义梳理一遍,再结合课文内容融入自己的理解,最终得到了他们的点头认可。一件事,纵使过程曲折,其中滋味却分明不同,就像豆花的老和嫩,经历的打磨也不同。
“而今尘尽光生,照破青山万朵。”心有所向,何惧道阻且长。只要我们保持坚韧,无论结果如何,都是对生命阅历的一种丰盈。于百折不挠后蓄力前进,对生活保持热爱和信心,我们才能走得更远、过得更好。
作者简介:蒋萍,笔名小夭,重庆市丰都县作协会员、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,作品散见于《中学生博览》《外国文学》《文学家》。现任教于重庆市丰都县三建乡蔡森坝完全小学校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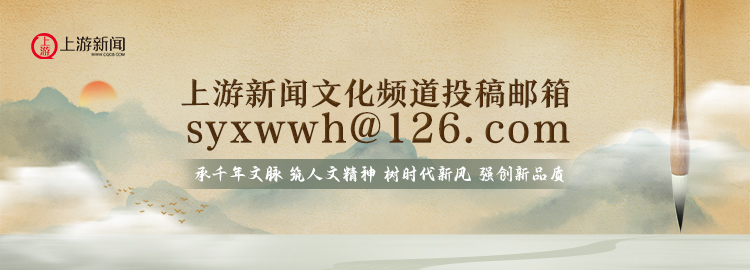
凡注明来源重庆日报的作品,版权均属重庆日报所有,未经授权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利用其它方式使用上述作品。已经本网授权使用作品的,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,并注明“来源:重庆日报网”。违反上述声明者,本网将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。
除来源署名为重庆日报稿件外,其他所转载内容之原创性、真实性、完整性、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,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渝公网安备 50011202500747号
渝公网安备 50011202500747号